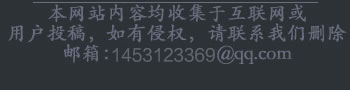seo三人行 > 新闻信息 > 正文
口述 | 贾玉芝 易杏英 郝尚勤 徐文燕 李晓冰 等
采访整理 | 杨玉珍
上世纪60—80年代出生的人,想必童年时代都听过一个儿童广播节目——《小喇叭》。“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嗒嘀嗒,嗒嘀嗒……”那清脆稚嫩的童声,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成为他们一生中挥之不去的记忆。一提起节目里的许多名字,如康瑛老师、徐文燕老师、孙敬修爷爷、曹灿叔叔以及木偶人物“小叮当”、邮递员叔叔等,人们的脑海中就会浮现出这些亲切可爱的形象,沉浸于对童年时代美好的回忆中。

学龄前儿童广播《小喇叭》诞生了
新中国成立后,百业待举,党和国家领导人从国家发展与民族未来考虑,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在这一背景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对少年儿童广播》于1951年5月1日开播,对象是小学及初中学生。后来,《对少年儿童广播》演变成两个节目《星星火炬》和《向日葵》,原来的栏目名取消。对小学和初中生的广播有了,学龄前儿童怎么办?在这样的情况下,1956年9月4日,《小喇叭》节目诞生。
主管《小喇叭》的第一任少儿部主任是郑佳同志。说起郑佳,在《小喇叭》工作过的人无不对她充满了感激与敬仰之情。她被公认为《小喇叭》的奠基人,没有她,就没有《小喇叭》后来形成的一套完整的工作制度和工作人员对节目精益求精的精神,也就不会有《小喇叭》后来的知名度。

贾玉芝(《小喇叭》原编辑,原少儿部主任):我是1955年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工作的,郑佳那时刚从中央电台记者部调到少儿部担任主任。郑佳是一位事业心非常强而且创新性很强的女同志。1956年《小喇叭》节目开播后,她提出了“开门办广播”的口号,要求我们到孩子当中去,到幼教工作者中去,广泛联系作家、演员以及其他行业的劳动者,依靠社会力量办节目。
郑佳十分注重节目的对象性,不管是内容、形式、语言、音乐,都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处处想的都是把最健康、最有趣、最容易被孩子接受的节目奉献给孩子。在郑佳长年累月的严格要求和言传身教下,少儿部的编辑队伍养成了敢想敢干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郑佳倡导的经过实践检验行之有效的一系列做法,逐步以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这些宝贵财富使《小喇叭》受益匪浅。《小喇叭》节目被评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十大节目之一。
为编出好稿子,去幼儿园蹲点是常事
嗒嘀嗒,嗒嘀嗒,我的名字叫《小喇叭》。一到时间我就来,你打开收音机我就说话。我要给你讲有趣的故事,还给你讲有趣的童话。我要告诉你月亮为什么圆又缺,星星的眼睛为什么直眨巴,燕子为什么秋天往南飞,青蛙为什么冬天不见啦。我要说谜语叫你猜,为了让你笑得流眼泪,我要给你说笑话。我要讲小白兔打败大灰狼,我要跟你一快唱1234,我要问你衣服是自己穿的吗,扣子是自己扣的吗,是谁自己穿的鞋和袜?别忘了我是你的好朋友,我的名字叫《小喇叭》。
这是《小喇叭》节目的开篇诗《小喇叭的话》,从这首诗大概可以看出《小喇叭》的定位和节目内容。它的知识性、趣味性,适应了那个年代信息匮乏、知识获取渠道单一的特点,丰富了孩子们的生活,教会了孩子们各种知识,获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广泛喜爱。很多小朋友很快就成为了《小喇叭》的忠实听众,每天时间一到,准时守候在收音机前等着收听节目。
节目的内容满足了孩子们的求知欲,丰富了他们的童年生活。但是,对《小喇叭》的编辑们来说,如何编出有趣的故事、讲出好听的童话,这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短短15分钟或20分钟的节目,凝聚了《小喇叭》编创人员太多的心血。
林阿绵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喇叭》。本以为堂堂最高学府的高材生到《小喇叭》工作很“屈才”,编《小喇叭》的稿子不过是小菜一碟,谁知实际的情况却大大出乎他的预料。
林阿绵(《小喇叭》原编辑):刚跨进电台大门,我血气方刚,雄心勃勃,自认为堂堂最高学府北大中文系毕业生,岂能编写不了给幼儿的广播稿?谁知眼高手低,一个月的实习下来,尽管费了不少力气,居然未能编出一篇像样的稿件。记得当时编过一篇《活捉鬼子官》的小稿,由于不了解幼儿生活,又不熟悉儿童广播特点,稿件送审了三遍都让部主任退了回来。正当灰心之际,组长贾玉芝就像老师给学生改作文一般,将稿件从头至尾细细修改一遍,还将抗日英雄“刘黑”的名字改成“刘红”,才使这篇习作得以播出。为了让我找到写稿子的感觉,少儿部让我和另一位编辑一起到东华门幼儿园去跟班蹲点学习。我们每天和孩子们一起上课、做游戏、聊天,有时也主动给孩子们讲故事,或者把编写的草稿念给他们听。这一个月的实习胜读十年书,使我对幼儿的心理、生理特征有了初步了解,对如何为他们讲故事也有了一些体会。
林阿绵提到的另一位编辑,是何先玉。她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喇叭》节目组,虽然工作两年后就调离了,但多年后依然感恩《小喇叭》,说在《小喇叭》工作的一段时光,为她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
何先玉(《小喇叭》原编辑):当时郑佳主任要求我们新来的同志一定要人手一个小本本,随时记录孩子们的表现,比如语言、动作、表情,熟悉孩子们的特点。这样做是为了改变我们在学校里已经习惯的学生腔,把我们的语言儿童化。这个改变是非常难的。当时我跟林阿绵去东华门幼儿园待了一个月,天天去,跟孩子们一块上课,观察不同类型孩子的表现,拿小本子记下来。后来我还到农村去,体验农村孩子的生活。后来又到工厂,到各种阶层中去。我记得去过石景山的工厂,住在工人家里,跟孩子们住在一块,跟他们一块爬山,一块到工厂劳模家里。我听郑佳老师的话,天天做记录,回来改变自己的文风。我原来写稿子是这么写,括号,寂静的夜晚,郑佳同志说,什么叫寂静的夜晚?学校中文系的那套东西搬过来是不行的,必须要用孩子的语言,孩子能理解的形象。给孩子们编故事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我当时被毙了好多稿子,返工稿更多。我记得写的一个配合雷锋宣传的童话故事广播剧改了六遍,最后是郑佳主任亲自改的。虽然当时感觉挺不容易的,但我要感谢《小喇叭》,因为那段时间给我打下的编辑基础是非常牢固的。
《小喇叭》的编辑们不仅到孩子们中间了解孩子的生活,很多编辑还和幼教工作者打成一片,经常组织他们开座谈会,有时为编辑一个小栏目,还经常下到劳动者中间去采访、去体验生活。编辑王成玉为了写关于赞扬全国劳模、北京掏粪工人时传祥的儿歌,曾经跟着时传祥同志一起去背粪。采访完回来,有了真实的生活体验,写出了“背着粪桶笑脸仰”等脍炙人口的语句。
编辑们的这些努力,连幼儿园老师都看在眼里,他们被编辑的敬业精神深深感动。
钱德慈(幼教工作者,《小喇叭》业余作者):我参加工作不久《小喇叭》就开播了,我当时待的幼儿园离石碑胡同特别近,所以经常带着孩子们到石碑胡同去录音。《小喇叭》的编辑们也经常到我们幼儿园蹲点学习,所以跟编辑们熟悉起来。大概是1962、1963年的时候,《小喇叭》有一个时间段是晚上7:30播出,其实这个点编辑们已经下班了,但为了跟孩子们一起听《小喇叭》,看孩子们能接受多少、理解多少,他们下了班继续工作。我有时候是上晚班,但编辑是八小时工作制,他们把八小时之外的时间依然奉献给了孩子们,我觉得特别难得、特别感动。他们还在实际工作中了解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们用什么教材,有一次发现了我给孩子们写的东西,他们就用了,还鼓励我继续给《小喇叭》写东西,后来一写就写了几十年。
了解了孩子们的喜好和接受程度,编辑们才能有的放矢对节目内容做出精心的编排。古今中外的内容都在他们涉猎的范围内,讲的故事里,中国古代的有西游记、三国、岳飞的故事,现代的有抗日战争、毛泽东周恩来的故事,外国的有《安徒生童话》《格林童话》等。编辑们不仅在原有素材上进行精心改编,而且还团结了一大批著名作家、诗人、作曲家为孩子们进行创作,著名作家刘心武、刘厚明,作曲家潘振声等人都为《小喇叭》创作过不少作品。为了节目的丰富性和多样化,《小喇叭》还请来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爷爷、著名演员瞿弦和叔叔、曹灿伯伯以及北京人艺的老演员们参加节目的播出,他们亲自审稿、参加录制和审听节目,大大提高了节目质量。这些艺术大师们绘声绘色、活灵活现的高水平演播,吸引了众多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着迷地收听。正如贾玉芝主任所说,那个年代《小喇叭》成了孩子们的精神寄托。每天《小喇叭》广播时间一到,家家户户都传出“嗒嘀嗒”“嗒嘀嗒”的声音,全国千千万万的小朋友都坐在收音机旁听《小喇叭》讲故事,跟着《小喇叭》说童谣、学儿歌。
停办十年之后的复播——木板房里的《小喇叭》
1966年,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浪潮扑面而来,连听众对象为学龄前儿童的《小喇叭》都受到了冲击。从1968年到1978年,《小喇叭》一度停播了十年之久,连《小喇叭》的名字都被改成了《红小兵》。
贾玉芝:“文化大革命”期间,《小喇叭》节目停播不是上面让停的,而是我们自己办不下去了,因为实在没法办了。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中央电台没有自己的东西,都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的东西,大家都说一样的话,都是一个声音。后来,《小喇叭》改成《红小兵》节目,因为《小喇叭》听着太“修正主义”了,改成《红小兵》就听着挺“革命”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小喇叭》播过王任重陪毛主席畅游长江的一篇通讯,那时候不能自己随便改,就照着新闻稿念。明知道孩子们听不懂,但也没办法。当时歌曲也只让播八首歌,如《大海航行靠舵手》《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等。
“文革”结束后,全国各地的老师、家长和小朋友纷纷来信,迫切要求恢复《小喇叭》广播。可是,那时候节目组的许多人都调到别的部门(组)去了,连办公室也没有。更糟糕的是,“文革”前多年积累的录音资料统统被消磁,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易杏英(《小喇叭》原编辑,原少儿部主任):“文革”期间,很多录音资料都被销毁了,留下来的只有像《小熊请客》这类“文革”中被批判过的节目。当时造反派说,《小熊请客》不好,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们还讲什么请客,你们要小心搞资本主义。《小喇叭》的同志就说:“正因为它们是大毒草,所以要把它留下,咱们好作批判用。”除此之外,其他讲故事方面的内容基本上都被销毁掉了。所幸的是,当时宁夏电台的潘振声同志保留了很多《小喇叭》的幼儿歌曲录音,他便给节目组复制了许多幼儿歌曲的磁带,解了《小喇叭》节目恢复播出后音响资料缺乏的燃眉之急。
1978年7月,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领导批准,少儿部抽出三位同志筹办恢复《小喇叭》节目。这三位同志在驻中央广播事业局警卫连战士的帮助下,在广播大楼的冷却池旁边空地上,盖起了木板房,这就是《小喇叭》节目组的办公室。
郝尚勤1978年从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小喇叭》。来之前,他有过犹豫,自己一个大老爷们,去干整天跟幼儿园小朋友打交道的工作,去还是不去?经过慎重考虑,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小喇叭》,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对于第一天走进《小喇叭》的情景,他至今还历历在目。
郝尚勤(《小喇叭》原编辑,原少儿部副主任):记得第一天走进《小喇叭》节目组,眼睛瞪得溜圆,怎么也想不到它会这般模样:一排高高的白杨树围着一个大水池,水池旁搭建着一排南北朝向的简易木板房。木板房里一道砖墙隔成里外两间,外间安放着两台机器和一张乒乓球台子,后来知道那是用来编辑广播节目磁带的机器和编辑部用来开会的桌子。木板房的里间是《小喇叭》节目组的办公室,铺着青砖的地面像是刚刚洒过清水,散发出水与尘埃混杂一起的气味。几张办公桌前坐着几位四五十岁年纪的老编辑。办公室虽说简陋,却很整洁,老前辈们热情得像邻居家的大爷大妈。从那时候起,我才知道在《小喇叭》里讲故事用的广播稿全都是这些老前辈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费尽心血编辑出来的。
经过三个多月的紧张准备,《小喇叭》编录了第一批节目。
易杏英:当时少儿部让贾玉芝组长、钟晓冬和我三个人筹办恢复《小喇叭》。我们首先去做调查研究,到幼儿园去开座谈会,了解孩子们喜欢什么,想听什么,有时候也把幼儿园老师请来台里一起探讨。经过研究讨论,我们决定先录一些对独生子女进行教育的内容,因为那时已经开始实行计划生育了。我们还把过去的稿子找出来,进行编辑加工后重新录音。钟晓冬跟外面演艺单位联系得比较多,她就找来曹灿等演员参加录音。
在各位工作人员的努力下,1978年11月6日,在停播十年之后,《小喇叭》终于恢复广播了。一时间,像雪片似的来信从四面八方飞到木板房。许多家长和老师带着欣喜的心情,写来了热情洋溢的祝贺信,有的老师激动得热泪盈眶,还有不少老师和家长以及听《小喇叭》长大的孩子,在来信中回忆起过去听《小喇叭》的收获和有趣的故事。当时的小朋友听到了“嗒嘀嗒”的声音,高兴地奔走相告:“《小喇叭》来了!《小喇叭》来了!快来听讲故事呀!”
那些熟悉的名字:康瑛老师、徐文燕老师、孙敬修爷爷、曹灿伯伯……
编辑们在幕后精心编辑创作出来的节目内容,必须通过前台的主持人或播音员传递给孩子们。相比于幕后默默无闻的编辑,演播人员更容易被小朋友们记住和喜爱。《小喇叭》的演播人员,人们熟悉的有康瑛老师、徐文燕老师、木偶人物“小叮当”、邮递员叔叔张文星,以及特邀艺术家孙敬修爷爷、曹灿伯伯、陈铎叔叔、瞿弦和叔叔等。
转载请标注:我爱技术网_SEO三人行——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 搜索
-
- 2018-11-20诺基亚12月新品发布会:或将推蔡
- 2018-11-20为真全面屏预热?三星被曝前置摄
- 2018-11-20iPhoneXS/XR终极防水测试:iPhon
- 2018-11-19“3D模术师”上线,仅Mate 20 Pr
- 2018-11-19Lingoes Translator 灵格斯词霸
- 2018-11-19安阳市政府网站
- 2018-11-19苹果新款iPad Pro今日首销:A12X
- 2018-11-19國內手機市場新品發布扎堆手機強
- 2018-11-19苹果新iPad Pro跑分出炉:A12X超
- 2018-11-19一加手机6T评测:论性价比和旗舰
- 2018-03-22白色情人节,用英得尔车载冰箱打
- 2018-03-22送礼不踩雷!白色情人节虐狗攻略
- 2018-04-09邪恶漫画:无人岛完整版,没看过
- 2018-04-10“江苏工匠”苏建时: 解决实际
- 2018-04-10CBA季后赛直播:山东男篮vs江苏
- 2018-04-10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新闻发布会
- 2018-04-102018年春节银联网络交易达6790亿
- 2018-04-10江苏首张增量配电许可证落户扬中
- 2018-04-10嘟嘟~您乘坐的旅游专列已抵达江
- 2018-04-11自治区旅发委发布2018年春节黄金
- 2018-11-20诺基亚12月新品发布会:或将推蔡
- 2018-11-20为真全面屏预热?三星被曝前置摄
- 2018-11-20iPhoneXS/XR终极防水测试:iPhon
- 2018-11-19“3D模术师”上线,仅Mate 20 Pr
- 2018-11-19Lingoes Translator 灵格斯词霸
- 2018-11-19安阳市政府网站
- 2018-11-19苹果新款iPad Pro今日首销:A12X
- 2018-11-19國內手機市場新品發布扎堆手機強
- 2018-11-19苹果新iPad Pro跑分出炉:A12X超
- 2018-11-19一加手机6T评测:论性价比和旗舰
- 网站分类
-